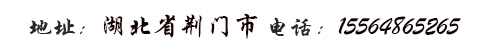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
|
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。 ▼ 自由可以呈显为痛苦和忧伤, 要不被痛苦和忧伤压倒的话, 那怕沉浸在痛苦和忧伤中, 又能加以观照, 那么痛苦和忧伤也是自由的, 你需要自由的痛苦和自由的忧伤, 生命也还值得活, 就在于这自由给你带来快乐与安详。 ▼ 自由不是赐予的,也买不来, 自由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意识, 这就是生之美妙,你品尝这点自由, 像品味美好的女人性爱带来的快感, 难道不是这样? 高行健高行健(-),法籍华裔剧作家、小说家、翻译家、画家、导演、评论家。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,年移居法国,年取得法国国籍。因“其作品的普遍价值,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,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”而荣获年诺贝尔文学奖,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语作家。直至年,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。代表作有小说《灵山》、《一个人的圣经》,戏剧《绝对信号》、《车站》等。 年,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。年,开始在巴黎郊区巴纽里定居,起初生活艰难。年,成为法国“具像批评派沙龙”成员,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。年,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“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”。年,加入法国国籍。年,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。 20世纪90年代期间,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。剧作如《生死界》、《夜游神》、《对话与反诘》、《周末四重奏》等。年2月25日,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“荣誉军团骑士勋章”。年,法国举办“高行健年”以表彰他的成就。 《一个人的圣经》节选他最终要说的是,可以扼杀一个人,但一个人那怕再脆弱,可人的尊严不可以扼杀,人所以为人,就有这么点自尊不可以泯灭。人尽管活得像条虫,但是否知道虫也有虫的尊严,虫在踩死捻死之前装死挣扎逃窜以求自救,而虫之为虫的尊严却踩不死。杀人如草芥,可曾见过草芥在刀下求饶的?人不如草芥,可他要证明的是人除了性命还有尊严。如果无法维护做人的这点尊严,要不被杀又不自杀,倘若还不肯死掉,便只有逃亡。尊严是对于存在的意识,这便是脆弱的个人力量所在,要存在的意识泯灭了,这存在也形同死亡。 自由短暂即逝,你的眼神,你那语调的那一瞬间,都来自内心的一种态度,你要捕捉的就是这瞬间即逝的自由。所以诉诸语言,恰恰是要把这自由加以确认,那怕写下的文字不可能永存。可你书写时,这自由你便成看见了,听到了,在你写你读你听的此时此刻,自由便存在于你表述之中,就要这么点奢侈,对自由的表述和表述的自由,得到了你就坦然。 说佛在你心中,不如说自由在你心中。自由绝对排斥他人,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,他人的赞赏,更别说哗众取宠,而哗众取宠总活在别人的趣味里,快活的是别人,而非你自己,你这自由也就完蛋了。自由不理会他人,不必由他人认可,超越他人的制约才能赢得,表述的自由同样如此。 他需要一个窝,一个栖身之处,一个可以躲避他人,可以有个人隐私而不受监视的家。他需要一间隔音的房间,关起门来,可以大声说话,不至於被人听见,想说甚么就说什么,一个可以出声思想他个人的天地。他不能再包在茧里!像个无声息的蚕,他得生活,感受,也包括同女人尽兴做爱,呻吟或叫喊。他得力争个生存空间,再也忍受不了这许多年的压抑,也包括重新醒觉的欲望,都不能不有个地方发泄。 当时他那个小隔间刚放得下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,冬天装上取暖的煤炉和铁皮的抽风管道之后,再多一个人在房里都难转身。简易的隔墙后面,那对工人夫妻夜里行房事和婴儿撒尿全都能听见。那院子还有两户人家,公用的自来水管和下水道都在院里。那姑娘每次来他这小屋都在左右邻居注视下,他得让房门半开,不是闲扯,便是喝茶。他结婚十多年来一直分居的妻子通过作家协会的D委就找居民委员会调查过,D什么都要管,从他的思想、写作到私生活。 这女孩来找他时穿的一身过于宽大的棉军装,戴的红领章,涨红个脸,说看了他的小说非常感动。他对穿军装的女孩有所戒备,又见那一副娃娃脸,便问她多大。女孩说军队医校还没毕业,医院实习,今年,说的是当年,十七岁了。他想正是女孩子容易动情的年纪。 他关上房门,同这姑娘接吻时还没拿到同他妻子离婚的法院判决。他屏息抚摸那女孩时,同样也听见邻居在院子里放水、洗衣、洗菜、往下水道倒脏水和过往的脚步。他越益明确,所以需要个家并不是拥有个女人,要的首先是一个不透风雨的屋顶和四堵封闳而且隔音的墙。可他并不想再娶妻,这十多年徒有法律约束的婚姻已经够了,他得放纵一下。对女人他心存疑虑,尤其是可能倾心爱慕的这种年轻漂亮似乎有出息的姑娘。他已经多次被出卖和告发过。 还在上大学期间,他爱上同班的一位女生——长相和说话的嗓音同样甘甜。这可爱的姑娘又追求进步,向D支部书记汇报思想,把他对当时共青团倡导青年必读的革命小说——青春之歌——的挖苦话顺带也报告了。这女生当然不是故意害他,对他也并非毫无情意,可越是多情的姑娘相反越止不住向D交心,如同有信仰的人需要向神父忏悔内心的隐秘。共青团支部便认为他思想阴暗!这还不那么严重,虽然他未能入得了团,大学还是让他毕业了。 严重的是他妻子,要是告发有据,拿到他偷偷写下的那怕是一张纸片,那年代就足以把他打成反革命。啊,那革命的年代,姑娘们也革命得发疯,革命得令人恐怖。他不能信任这么个穿军装的女孩子。人来向他请教文学的,他说当不了老师,建议去大学夜校。现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班,交点钱就可以报个名,过两年还能多拿个文凭。这女孩问他读些什么书才好?他又说最好别读教科书,图书馆大都已重新开放,是凡以前的禁书不妨都可找来看看。这姑娘说也想学习写作,他劝说她最好别学,弄不好只会耽误前程,他自己就麻烦不断。这么单纯的女孩,穿的军装又学了医,前途就很有保障。可这女孩说她并不那么单纯,不像他想象的那样,她想知道更多的东西,想了解生活,这同穿军装和学医并不矛盾。 他对这女孩并不是没兴趣,可他宁愿同在社会底层泥坑里滚打过的那种滥妞轻轻松松做场爱,不必费口舌去教这女孩什么是生活,而何谓生活?只有天知道。 他无法对来求教的这女孩解释什么叫生活,更别说何谓文学,恰如他无法向领导他的作家协会D的书记解释他之所谓文学,无需由谁指导乃至批准,因此,他才屡屡倒楣。面对这么新鲜可爱的姑娘穿的那身军装,他动不了心思,更没有遐想。他没有想到碰她,更没想到同她上床。这女孩来还从他书架上取走的几本书,说都看了,面孔红扑扑的,刚进门还微微喘息。他照样给她泡上一杯茶,像接待约稿的编辑那样让她在房门背后靠书桌的椅子上坐下,他则坐在书桌前的另一把靠背椅上。 这小房里还有一张简便的沙发,那时已破旧,屋里安上了取暖的煤炉,沙发便挪到紧挨床头的墙边。要让这女孩坐到沙发上,煤炉上安的铁皮抽风管道便挡住脸面,谈话不很方便。他们就都坐在书桌边,这女孩手还在抚弄还来的那几本因为反动和色情曾经招禁的小说,就是说,这姑娘已经尝了禁果,或者说知道什么是禁果才这么不安。 他注意到这女孩的肌肤始于那纤细柔嫩的手,近在咫尺,还不停抚弄书。这姑娘也注意到他在看她那手,便把手收到桌面以下,面孔就更红了。 他开始询问女孩对书中的主人公主要是对女主人公的看法,那些书中女人的行为都不符合当今的道德和D的教导。他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生活吧,生活并没有尺寸。这姑娘有一天要也揭发他,或是她服务的军中D组织命令她交代同他的往来,他这话也没大错,他已往生活的经验就这样时时提醒他。啊,那也叫生活!这女孩后来说毛主席也有许多女人,他才敢于吻她。女孩也闭上眼睛,听任他抚摸宽大的军棉衣里敏感得像触了电的身体。当时,这姑娘问还能不能再借本这样的书给她看?说她什么都想知道,这并没什么可怕的。他这才说要是书籍也成为禁果,这社会就真可怕,终于宣告结束了的所谓文革,多少人因此葬送了性命。女孩说这她都知道,打死的人她也不是没见过,乌黑的鼻血叮满苍蝇,说是反革命没人收尸,她那时还是小孩子。可别把她当孩子了,她已成年。他问成年又意味什么?而她说别忘了她可是学医的,抿嘴一笑。他随后捏住她手,吻到了他渐渐松软的嘴唇。之后,她时常来,还书借书,总在星期天,待的时间越来越长,有时从中午到天黑,但她必须赶晚上八点的班车,回远郊军营驻地。总是在天黑时分,院子里打水洗菜的声音渐渐稀疏平息,邻居也都关上房门,他才把门缝合上,同她亲热一下。她也从未脱下军装,看着桌上的钟,末班车的时间快到了,便匆匆扣上制服的纽扣。 他越加需要一间能庇护隐私的房间——好不容易拿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、依照官方对生活的正统观念提出要结婚,并且说女方同他结婚登记的条件,是他得先有间正经的住房。他已有二十年的工龄,包括文化革命中弄去农村改造的那些年,按有关分房的文件规定,早该分到住房。 可他还得折腾两年多,同管房的干部大吵大闹了不知多少几回,赶在领导作家协会的更高的D的领导对他下手批判之前,总算争得了一个小套间。动用了他全部的积蓄,还预支了一本书的部分稿费,且不管这书能否出版,好歹安置了一个小安乐窝。这姑娘来到他新分配的房里,房门的弹簧锁刚碰上,两人便激动得不行。当时还没粉刷完,满地的石灰浆,也没有床!就在一块沾了石灰的塑料布上,他剥光一直藏在宽大的军服下还是少女那细条条的身体。但最,这姑娘求他千万别进入她身体里,军医院有规定,每年要作一次全面的体格检查,未婚的女护士还得查看处女膜是否无恙。她们服役前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,除了日常的医务工作,还随时可能有军事任务陪同首长出差,以保证首长们的健康。她许可的结婚年龄为二十六周岁,结婚对象得经部队领导批准,之前不得退伍,据说有可能涉及国家机密。他什么都做了,只没有插入,或者不如说他遵守诺言,虽没有插入其他能做的却都做了。不久,这女孩果然接到军务,陪同部队首长去中越边境视察!使断了消息。将近一年之后,也是冬天,这姑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他是半夜里从一位朋友家喝酒刚回来,听见有人轻轻敲门。这姑娘哭丧个脸!说在外面等了足足六个小时,都冻僵了,又不敢待在楼道里,怕人看见问她找谁,只好躲在外面的工棚里,好不容易才见这房里灯亮。 他连忙关上房门,拉上窗帘,这姑娘娇小的身子裹在宽大无当的军大衣里还没缓过气来,就又被他在地毯上操了她,翻来覆去,不,翻江倒海、光溜溜像两条鱼,不如说像两头兽,撕裂,肉搏一阵。她嘤嘤哭了,他说放声哭好了。他说他是一头狼。她说不,你是我好哥。他说,他想成为一头浪,一头凶狠贪婪噬血的野兽。她说她懂他哥!她就是她哥的,她什么也不怕了、从今以后只属于他哥,她后悔的是没早给他,他说别说了。之后,她说要她父母无论如何想让她离开部队。其时,他得到国外的一份邀请而不能成行。她说她可以等他——她就是他哥的小女人。而他终于拿到了护照和签证,也是她催他快走,免得变卦。他没想到这便是永别,或许不愿不肯这样想!免得触动内心深处。他没有让她来机场送行,她说也请不了假。从她的军营即使乘早晨头班车进城,再转几次车到机场,在他起飞前赶到估计也来不及。 这之前,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这国家,只是在飞机离开北京机场的跑道,嗡的一声,震动的机身霎时腾空,才猛然意识到他也许就此,当时意识的正是这也许,就此,再也不会回到舷窗下那土地上来,他出生、长大、受教育、成人、受难而从未想到离开的人称之为祖国的这片黄土地。而他有祖国吗?或是这机翼下移动的灰黄的土地和冰封的河流算是他的祖国吗?这疑问是之后派生出来的,答案随后逐渐趋于明确。 当时他只想解脱一下,从笼罩住他的阴影里出国畅快呼吸一下。为了得到出国护照,他等了将近一年,找遍了有关的部门。他是这国家的公民,不是罪犯,没有理由剥夺他出国的权利。当然,这理由也因人而异,要找个理由怎么都有。 过海关的时候,他们问箱子里有什么?他说没有违禁的东西,里面有什么? 砚台,磨墨用的。新买的一块砚台。他意思是说不是骨董,不在查禁之列,可他们要扣下他尽可以找任何藉口,他毕竟有些紧张。一个闪现的念头:这不是他的国家。 同时,他似乎听见了一声“哥”,他赶紧屏息,镇定精神。 终于放行了,他收拾好箱子,放到传送带上,拉拢随身的旅行袋的拉链,转向登机口。又听见一声喊叫,似乎在叫他名字。他装没听见,依旧前去,但还是回了一下头。刚检查过他行李的那主看的是板壁隔成的通道中几名外国人,正在放行。 他这时又听见长长的一声,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,声音来得很远,飘浮在候机大厅哄哄的人声之上。他目光越过入关处的板墙,寻找声音的来源,看见二楼汉白玉石的栏杆上伏着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,戴的军帽,却分辨不清面目。 同她告别的那一夜,她委身于他时在他耳边连连说:“哥,你别回来了,别回来了……”那是她预感——还是就为他着想?她比他看得更透?还是对他心思的猜测?他当时没有说话,还没有勇气下这决断。但她点醒了他,点醒了这个念头,他却不敢正视,还割不断这情感与欲望的牵挂,舍弃不了她。 他希望伏在栏杆上那绿军装的身影不是她,转身继续朝登机口去,航班的显示牌上红灯在闪光。他又听见身后一声分明绝望的尖叫,一声拖长的”哥——”那就肯定是她。他却没有再回头,进入登机口。 : 《一个人的圣经》 作者:高行健 原编文章,欢迎转发 未经允许,严禁转载 ▼ 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aosengyuanji.com/xzyj/275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说说佛教高僧坐缸的事情
- 下一篇文章: 高行健文学的理由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演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