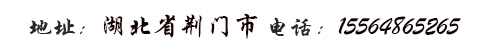凌晨三点半
|
云南白癜风微信交流群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lx/150217/4580350.html 躺了四个钟,脑袋里好像沉淀干净了,只是躲躲闪闪,还没跌进睡眠。 “天知道他为什么变成了一只蚊子......”收拾完脑子里的胡言乱语,起夜。打开蚊帐,一件一件辨认地面的物体,桌子、水桶、行李箱,没有异样。下床,脚触地时打了个寒颤。穿上并不常穿的厚外套,带上手机,开门,走廊亮着灯,对面楼的楼梯也明晃晃地扑过来。吹来一阵感觉不到温度的风,你隐约看见左手边的人形,像是要牵引着你到哪儿去,呼,原来是衣服。极目远眺,两端都是空荡荡的走廊尽头。 “我没有什么遗憾了......”尽头的墙壁牵引着脑子陷进苍老的声音里,呆滞间突然掉落出一句话来你差点脱口而出:“死神在找我。”你跑进迟钝的记忆库里探寻辟邪方法,嘴里便蹦出“心诚则灵”。回想,“心诚”的是什么,连上默念的上一句话:“死神在找我,心诚则灵”。呸,重说一遍,死神找不到我,心诚则灵(此时你想起,《哈利波特》里法术高超的邓布利多能一眼识破哈利的隐身衣),又改口道:“死神不找我,心诚则灵。”一路念叨着到厕所。像是有人用力捶门的声音,第三间的门倒落,滑了出来。不知道愣了多久,回过神来后走前去,用视线一寸一寸把厕所的角落穷尽。倒落的门里没有东西;第四间靠墙,窗户外的黑暗说不定会生出些什么来;第一间的门半掩着,好似能看见进去后一只手从门下的缝隙穿入的画面;第二间的门缝因第三间先前的动静还在微微开合着。拿手指戳开第二间的门,四方形地面展露无疑后,脚却被“钉”在了原地。不然还是回宿舍憋着?可是走回去也很难,即使能安然躺在床上,会不会下半夜就膀胱胀裂而死,还落下一个小便失禁的遗体和脏污的衣物。 “我没有什么遗憾了……”声音又一次自顾自地响起。还是搏一把!想想马克思!唯物主义!恐怕会触怒神灵……那想想《圣经》!马太福音!他们会不会是同一批、只不过不是同一原产地?思来想去,这才找到一个救命点子——“厕所神,厕所神,承蒙您庇佑,保我周全!”一鼓作气,进门,锁上……其间死死盯着两边隔板的间隙,呼,没有露出影子来。 她用手掌捂着蹲下身时隐隐作痛的膝盖。 脸上盖着的草纸越压越低了,原本还能看见耳朵的,现在一整个头都被埋进草纸里。妯娌在打赌,看谁敢掀开老人家脸上盖着的草纸。 “切,这有什么不敢的,要就一起去。” 她们一起跪到老人家旁边,“爸,打扰你了,我们想再看看你的样子,就掀开来看看,你不要生气。”说完以后两个人都看向了对方,没人向前,相视一笑,打闹着退回墙边。 “……我以后再也没有阿爸了……你怎么抛下儿子孤孤单单留在这里……”儿子和妯娌们坐在席子上,听门口的喇叭一遍一遍播着这些哭丧的音乐。 门外的叔侄掀开灵堂的蓝布,露出半张脸,低声说:“有人来了。”扑克收起来,手机放下,依据男女长幼找到自己的位置,跪下,面朝两张长椅上躺着的老人。脚步声近了,呜咽声、眼泪、悲痛,在这一刻准备齐全,蓝布一开,一齐奏响。 这是守丧第二天。 哭丧的音乐在脑子里循环起来,厕所门挡在眼前,手停在把手边上,半张着。先转移注意力,想想睡前喝的那杯奶茶,捧着奶茶走过的园东湖,稍稍平静了,恐惧也被忘却了,于是继续念厕所神的庇佑,哗的一下,回到厕所外的世界。厕所门口对着楼梯,一个通向上,一个往下延,摆在面前的,显然是末路最急切的选择。腿又开始很不争气地软了。 天知道他为什么变成了一只蚊子。这儿的人们常常把飞蛾或螳螂当成刚死去的家人,他一直也这么以为,可现在,头七这天的晚上,他却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只蚊子。原因只有天知道,他只能揣摩一点天意,大概是断气时脑子里最后一点想法被天听见了吧。 心想着,这些不争气的子孙,要是能最后给他们一点告诫就好了,扇一巴掌、骂一通、或是像根针一样扎醒他们,就这么想着,想着,就在旷野长长的路上调转了方向,带着蚊子尖尖的嘴落在家门前。 他从门缝飞了进去,所有灯都开着,饭桌上摆满了菜,豆腐、猪蹄、腐卷、年糕,留给远行客的最后一顿,全没想到远行客此时长着蚊子的嘴。他飞进大儿子的房间,夫妇俩和几个亲戚坐在藤椅上,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机,一声不吭。他想起以前他们叽叽喳喳的样子,“我一走,他们倒是消停了。”房间忽然喧闹起来,有人惊呼:“老人家死了还在保佑我们!”他疑惑地停在半空,难道他们认出我了?他环顾房间,搜索声音的来源,是大嗓门的妯娌在说话:“老人家传下来的所有子孙的生肖——就是这期六合彩的生肖!” 脚边吹过一缕一缕的风,她的眼睛又一次呆滞,被钩在白白的墙壁上。“我没有什么遗憾了。”怎么可能会没有遗憾呢,米糊太咸了,被子不够暖,或是一早醒来想到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在人前唱过歌,今天唱一首给你们听吧,然后张开了嘴,用力开合,大儿子看见了,问“爸,要换尿布了是不是?”于是身子被翻过去裤子被扒下,张开的嘴忘了合上口水沾湿了枕头。或是最后,想叫一声“秀英”,却再也发不出声音了。 她深知愧疚能吞没一切理智,于是逃避、逃避,愧疚像是变成了一个黑洞,时刻要把她抽离出身体。掏出手机想给爸妈打电话。“妈,我害怕,我好害怕。”爸妈的手机一定都放在客厅,妈妈被吵醒,出来接电话,看到来电显示,她脑子里肯定一片空白,或是映着白白的病房、白白的病床。不该叨扰,该忍耐,肯定会过去的,怕或是不怕、走还是停,天都会亮的。“可是我害怕,我害怕……”一直响着,在耳朵里来回激荡。 他飞回静悄悄的走廊,从楼梯的扶手穿过,停在小儿子的门前。门里没有光,他们大概已经睡了。他从门缝潜进黑暗中,听见二人的呼吸声。他向床边透光的窗户飞去,靠近床沿时才看见在月光下潮汐一般起伏的被子。他匆忙往窗外飞去,听见房间里渐渐没了动静。 “唉。”房间里传来轻轻的一声叹息,是小儿子的声音。 “怎么了?” “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。” “哪儿?” 小儿子倒在床上,望着空落落的天花板,手掌捂在胸前,说:“这里边。” 她把手机塞回外套,犹豫之间,手指被口袋里一个纸质的尖角碰疼,摸出来,一小块红色三角,上面写着黄色的楷体字——“平安”。 那是出殡那天奶奶让她揣着的平安符。 妻子与妯娌彼此之间的冷嘲热讽蛛网似的遍布家中四壁,他逐渐明白一家之主的晚年生活理当与对话保持距离,关上电视机后耳畔的留白只交由红色收音机填补,他用二十年晚年生活学习沉默与平静,终于在八十一岁时结课。这一年,他因萎缩失去了嗓音与听力。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。 “你爷爷等了你好久,已经睡了,明天再去见他老人家吧。”我跟着妈妈一起上楼,经过爷爷的房间,安安静静的,后来才想起,那是因为没听到他平常睡觉能传遍整个屋子的呼噜声。 第二天被拉进房间的时候,奶奶正在给爷爷翻身,因为躺得太久,背上的肉已经躺烂了。他的头转过来,看着我,像个孩子一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,好奇、惶惑又无辜的眼神。 “阿公”我竭力掩饰心里的陌生感。 奶奶问他:“还认得出来这是谁吗?”“怎么会认……不出,”他把手举到半空,摆出一个变形的大拇指的手势:“我燕燕是这个。” 他从窗户进到楼下的客房,才知道她为了摆脱他离开后躺在半边双人床彻夜的失眠,从原来的房间搬到了这里。她戴上眼镜,坐在床上看六合彩图纸,像是过去六十年的每个夜晚那样。他悄悄落到她的肩上,看她的头发、耳朵、脖颈、正在写字的枯瘦的手。她在写什么,他飞近了些,却发现不过是阿拉伯数字在依次排列。 嘶——他忽地感觉到一阵剧痛,像是被撞在了什么金属硬物上,他又一次掉出了身体。 他回头望,看见被砸烂的那具蚊子的身体,和旁边老太婆手指上那枚金色戒指。 “老太婆,我走了,要多晒太阳。”他像氢气球一样向外飘去,却听见屋内传来弱弱的一声:“是你吗?” 天刚蒙蒙亮,四寂的田野听见贴着白对联的那个房子里又传来哭声。 好想说声,“不是”。 所有思绪都留在黑夜,人只记得昨夜失眠,上了个厕所,继续失眠,在幻想爷爷头七那天出现在房间里的一只蚊子。天亮的时候,一切都从阴暗的屋内抱出来,晾在阳光下,拍一拍,灰尘飞扬在暖洋洋的空气里,都能溢出笑来。可是,守在黑夜里的他们说他们的眼——糊上了一层明纸的窗,窗外有一只大大的手电向着这里照,那只苍老而温柔的手,他们害怕。 长 按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aosengyuanji.com/jgyj/902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每日功課佛说阿弥陀经要解31
- 下一篇文章: 好诗不过近人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