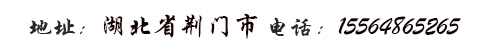微middot虚构巫宏振流园
|
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jzkbdfyy/ PhotobyMelissaReginaonUnsplash 微·虚构 本期作者 巫宏振 巫宏振,生于广东英德,九零后,小说散见《作品》及豆瓣网等。先后毕业于肇庆学院,中山大学。现住广州。 流园巫宏振 父亲去世前跟我说了一个秘密。这个秘密在他心里藏了六十年。他再三嘱咐,一定要回老家找到那家人,告诉他们当年的真相,再代他道个歉,赠送一笔精神损失费,做为迟到的补偿。 我在脑海里梳理了五六遍父亲留下的遗嘱,深思熟虑了几天,终究父债还得子还。我决定履行对父亲许下的承诺。 周五下午,我提前离开报社,回家捡了几件随行的衣裳,跟老婆和儿子告了别,驱车离开市区,赶往乡下老家。 到达老家东乡镇已是傍晚,我在紫荆街找了间家庭宾馆寄宿。宾馆房东很热情,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的客房。当天晚上,我向房东打听了近些年关于桃园村的事。房东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矮墩男人,与我的年纪相仿。 他嘴里叼着中华烟,眯着眼睛说:“早荒了,没人住了。” 我诚实地告诉他:“明天早上我要去桃园村走一趟。” 他把烟碾灭,丢在烟灰缸里,哼声一笑:“你们城里人真搞笑。没进城吧,就想要进城,进了城吧,又想念乡下。我也是从桃园村搬出来的,倒是没想过要回去走一趟。” 他的语气带有嘲讽的意思。 第二天,我早早起床,简单洗漱完毕便下楼去。街上阒寂无人。道路两边正在建设的小区楼房隐没在浓雾当中。走到一个岔路口,我看到路边竖起了一块小区建设的规划图。在那张图里,我看到了桃园村的位置。 我依着记忆,认出了进入桃园村的路口,沿着一条迂回的碎石路走进去,穿过一个杂草丛生的桃园。浓雾弥漫,眼前一片混沌。摸着朦胧,走到碎石路的尽头,便看到了晒谷场旁边的一块英石。那便是村口了。英石上面镌刻着三个斗大的隶书字:桃园村。 父亲告诉我,桃园村里还住着一户金姓人家,也就是父亲要我代他去寻找,去道歉的那一家。 金家住在桃园村的西头。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逶迤而下,延伸到了金家门口就被截成两段,一段通往村落尽头的翁江河,一段则通往金家的篱笆院子。院门紧闭,距离木门两步之遥还有一条不足半米宽的水渠。两间相连的瓦房建在低矮的地方,背后是隆起来的高坡。高坡上葱郁的常春藤攀沿下来,爬在房顶上,缠绕着正在袅袅升烟的烟囱。 我停在门口踮起脚尖往院子里张望。院子里传来咯咯的鸡叫声,估计是鸡群争食的时候踩翻了不锈钢的鸡盘,扑棱棱的声音混成一团。这时候,一个老妇人从院子右侧的厨房里慢跑出来,嘴里学着“咯咯咯”的鸡叫声,手里握着一根冒烟的柴棍。她的脚步很轻快,不像是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。她朝鸡群中跑去,垂在两鬓的一绺银发在稀疏的晨光下随风飘拂。 老妇举着搅火棍朝鸡群挥舞,把轰在一团啄食的鸡群吓得四处飞散。鸡盆倒过来盖在地面上,混了糠皮的鸡食散了一地。她蹲着用手把鸡食扒回到盆里。 我扶着院子的木门窃窃地往里面瞄。蹲在龙眼树下的黄毛狗嗅到了我的气味,霍地跳起来冲我发疯似的咆哮。 “唉呀,你们怎么又来了。我说过我不稀罕你们的施舍,反正我已经是一副老骨头了,死也要死在这里。”老妇看到我,不由分说地挥着搅火棍对我指指点点,一边顿着地面,一边冲我嚷。 “这是金有福家吗?您是周美玲周阿婆吗?”我踮着脚尖,隔着木门喊。 我需要一个走进院子的理由。 “周阿婆,我是从城里回来探亲的,是个记者。” 我手里还拿着一份从宾馆前台取来的《英城晚报》,恰巧该期刊登了一篇我写的新闻稿,是关于贫困户现状的访谈与调查。我扬起手里的报纸故意让她看到,即便我不确定她能否看到。 “你是谁啊?找我有什么事?”她问。 周阿婆取下铁钩,挪开木门,允许我走进院子,直接引我走到正屋门口停住。她用搅火棍敲了敲放在一边的矮凳子,示意我坐那里。她先坐到了一张竹椅上,双手还抓着搅火棍,一动不动。我也坐下了,眼睛环顾四周,院子的西角摆放着犁和耙,旁边是一个石棉瓦盖的牛棚,里面没有牛,一个装着铁轱辘的水井上还悬着一只生锈的锡桶。不仅是屋顶上爬满了常春藤,墙壁上的裂缝也钻出了一撮撮的嫩草,像是在争夺生存空间似的。 “我家原本也是在东乡镇的,后来搬进了县城。我听家人说起过您家的事。这趟回来也特意想采访您。” 我的手肘支着膝盖,身体前倾,音量稍大,确保她能听清楚我说的每个词。我的每个词都说得很仔细、谨慎。 “你不需要冲我大声喊。我都听得清楚,一字不落。你找我有什么事?”周阿婆蠕动了几下嘴,像是在嚼着什么,实际上嘴里空无一物。 “桃园村都荒废了,您还守在这里,为什么没跟村里人一起离开呢?”我问道。 周阿婆半眯着眼,蠕动着陷进去的嘴唇,好像没想要回答我的疑问。屋顶上的常春藤随风莎莎作响,像是生长的声音。此时,周阿婆的沉默让我看到,她已经停止生长,但是她那遥望的目光却依旧坚挺。老而坚实,也许是另一种生长。 “我还听说了金叔叔的事情。”我继续说,想要一点点地撬开她脑海里的记忆,跟她搭上话题。“跟您一直坚守在这里有关吗?” “你采访我这些事有什么用?能解决问题吗?”周阿婆说。她没有冲我嚷,“都是些陈年旧事了,谁晓得去管。” “但是您拒绝搬离桃园村,还拒绝了他们给您家提供的新房,这又是为什么呢?”我继续深问下去。 父亲只是告诉我他当年做的那件事,并没有再透露更多的细节。 “为什么?为什么?”周阿婆提高声音,重复着我的话,表示她的不满。 “听说今年年底,他们要把桃园村改造成生态小区,这里将会被夷为平地,建起一栋栋的楼房。可能到时候,您也要被迫搬走。”我的目光随之望向外面,“电视塔那边的山脚下新建了一个桃源小区,住了很多桃园村的人。听说他们也安排了一间两居室的房间给您。” 我像是一名被派来说服周阿婆搬迁的人。 “我家不去住。”周阿婆打断我的话,斩钉截铁地说。“他们多次来找过我,我都放话了,不给我家一个说法,不给老金一个安息的解释,我宁死不搬。” 她的语气很坚定。父亲生前一直为那事懊恼,弥留之际还再三嘱咐我要替他赎罪,追加补偿。直至归于尘土,他也觉得往事没有随风而逝,甚至会潜入下一代人的血液里。此刻,父亲仿佛就在一股风里,在偷偷地听着我跟周阿婆的谈话。 沉默了片刻,周阿婆似乎放低了警惕,说:“我家老金是被小人害的。一九五八年十月份,他被民警抓走的时候,才二十七岁。当时我怀着第二个孩子。他们没敢动我。”她停顿了会,像是陷入了回忆里,“一个星期后,法院判决书出来,判他是地主的儿子,是地主身份,有罪,要接受改造,还说他在排查的那段时间还故意隐瞒了身份,有图谋不轨的嫌疑。” 我插入一句话:“判决书里面写的是事实吗?” 周阿婆冷笑了一声,裂开了起皱的嘴唇:“老金的爸曾是国民党人,也做过地主,但是后来经人劝说,他爸弃暗投明,成了一名共产党员,投到邬强的队伍里。一九四四年,日本人打到粤北,他爸还立了功劳,带着一村人躲进山坳里。建国之后,他爸离开队伍,回到了老家,做了农民。他们说老金是地主身份,实际是在指他爸的地主身份。他爸回来之后,地主都被消灭了。户口登记时,老金也写了‘农民’,当然就是农民身份。谁料到,老金命不好,遭到小人的诬陷。” 我垂着头,目光落在脚下一坨干透的鸡屎上,有两只屎壳郎正在滚屎球。思忖了几秒钟,我抬起头问她:“知道那个小人……那个告密者是谁吗?” 她摇摇头说:“不知道,他们都很保密,守口如瓶。” “那金叔叔后来怎么样了?” “判决书出来一个月后,他被押到英德火车站,送到青海省的一个劳改农场,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……” 说到这里,周阿婆忽然停住了,她望着院墙外面长满野草的山坡与房屋,嘴唇微张,像张开的蚌壳,仿佛在细细地倾听野草生长的声音,细微而清朗,它们一撮撮的正在破土而出,顶破院子的地面,露出芽尖。 我的目光从那撮娇嫩的芽尖上移开,一同投向院墙之外,暖阳高照,宛如给桃园村盖上一层如纸一样薄的金沙。 “他没有给你们写信吗?” 周阿婆沉默地摇摇头,目光从院墙外收回来:“抓走这么多年,我没有收到一封信,连一句口信都没有。他在劳改农场的情况,我是从一个老乡那里听来的。那位老乡被打成‘右派’,也被押到那里改造,熬到了刑满释放的日子,活着回来了。” 周阿婆说那个被打成“右派”的老乡在前几年离世了。离世前,她还去看望过他。他的晚年过得幸福平静,没大病大灾,身边围着一群孝子贤孙,为他默默地悼念,也许这是他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:一代又一代,生生不息。 “他走得很安详。”周阿婆说,接着补充道:“可是老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” “那个老乡跟您说了什么?”我问她。 我听过父亲说起过那个老乡,他以前在韶关经营着一家私营煤炭厂,规模很大。后来公私合营,工厂被取代,他遭到辞退,由一名不懂经营的人接管了他的工厂。他携家眷返回桃园村,但是最后“搞资本主义”的罪名依然成立。 周阿婆说:“第三年,老金死在了逃离的路上。” 她说到这句话的时候,嘴唇在微微打颤,目光依旧坚挺。我没有再问什么,都陷入一场持久的沉默之中,像是一种悼念。 这时,身后传来一个短促的声音。我回头瞧过去,屋里走出了一个男人,他胡子拉碴,看起来就像脸上长着一撮烧焦的杂草。他就是周阿婆的二儿子,大儿子早早夭折了。他一直躲在门后偷听。他穿着一件灰色毛衣,留着平头,背微驼,正扶着门框朝我看过来。他长有兔唇,露出了一颗焦黄的门牙。没等我打招呼,他就朝厨房走进去了。周阿婆唤了他几声,也没有搭理。 傍晚六点多,我回到了宾馆。房东和家人正在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aosengyuanji.com/rlyj/785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喜了合集
- 下一篇文章: 历代高僧大德的故事敬安2